第二届中国当代实力派优秀作家 刘瑞敏
更新时间:2024-09-19 关注:3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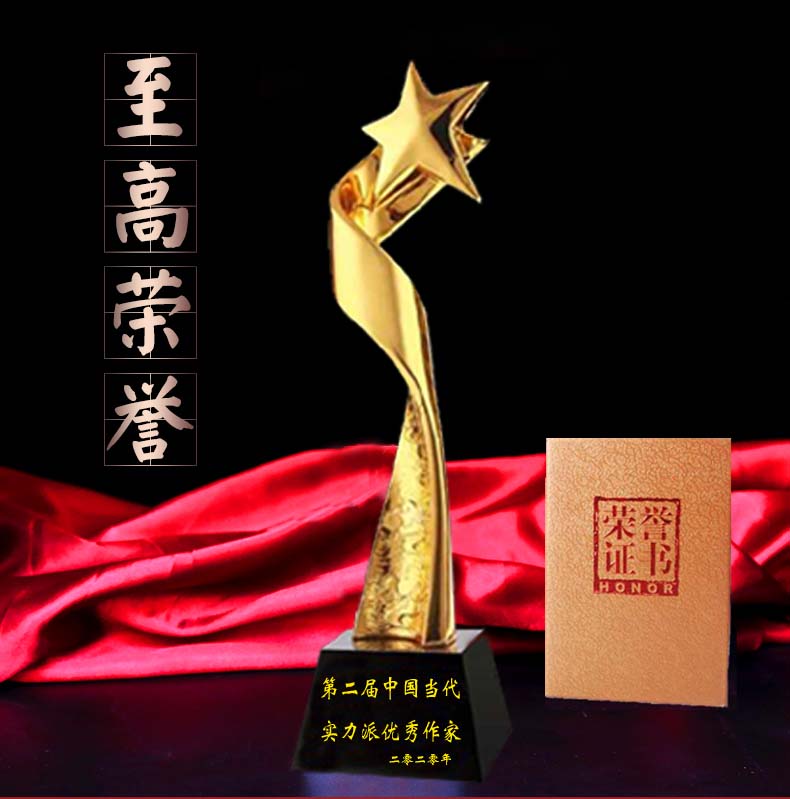

刘瑞敏,男,中共党员。1956年6月5日出生,天津市蓟州区人。中央党校在职本科学历,曾在齐鲁石化公司胜利炼油厂党委办公室,劳动服务公司。齐鲁石化公司厦门,深圳办事处等单位任秘书、经理、主任等职务。现为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南国文学《西部散文选刊》编委。散文《恍如隔世》获临淄区国庆征文征文三等奖,诗歌《游子回家》获得艺术人物杂志社,澳门回归20周年,“回归复兴”征文活动一等奖,并获“中华文化传播者”荣誉。作品:表演唱《老头老婆逛峱山》《“四德”花开咱村镇》获青州市群众文艺汇演创作演出二等奖。现代吕剧《劝爹》获中国(临淄)齐文化艺术节文艺创作二等奖。长篇小说《齐韵油魂》(47万字)2019年出版发行。《一位值得怀念的老人》(散文)《永恒的纪念》(诗文)等在《齐鲁石化报》《金夕阳》刊物登载。在厂党委办公室工作期间所写企业管理方面的文章在部级刊物发表。
作品赏析
天 眼
文/刘瑞敏
母亲曾多次对我说:“你是奶奶带大的,小时候你特别淘气,奶奶看你没少操心受累······”母亲的话我特别信,因为小时候的一些事,我至今还隐约记得些,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当淘气的时候奶奶就会说:“再淘气,老天爷打雷了。”一听到这句话,我就吓得不敢再淘了,装得“乖”起来。
老天爷何许人也?姓氏名谁?我一概不知,只知道他是自己心中最厉害的了,比爷爷还厉害,是自己最怕的了。
每次听到那“隆隆”的雷声,我就吓得萎缩在奶奶的怀里一动不动,这时候奶奶便轻轻拍着我说:“别怕,老天爷有眼,他不伤听话的孩子,你往后还气奶奶不?”我看着奶奶,小脑袋瓜摇得像波浪鼓似的。
“老天爷有眼”,这是我童年时,在奶奶身边听到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那时候村里还没通电,天一黑,家家户户都点了煤油灯,也叫洋油灯,那是因为点灯用的油都是从外国洋人那进口的。
庄户人吃晚饭一般都挺晚,吃完了饭,喂罢了猪,堵好了鸡窝,要是天气不好估摸着夜间有雨的话就再备点柴火,怕是明天没有干柴烧不成饭······把这些活都干完了,也就差不多该睡觉了。
爷爷和奶奶有个习惯,睡觉前总是炕头(挨着炉灶的那头)一个,炕捎一个,坐着唠一会儿嗑才睡呐,为了省点儿灯油,他们总是摸着黑儿唠。
“文革”初年,我上一年级了,不再依偎在奶奶的怀里听他们唠了,变成了和家里的小猫一起躺在奶奶的身边听,有时候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记得,爷爷奶奶唠的最多的就是有关大伯父的事。
奶奶说:“我就不信,咱的儿能是叛徒,他可不是那种人。我的儿,是啥脾气、性格,我还不知道吗!?当兵一走就这么多年,连一点音信也没有,村里像他这个年龄的,人家都成家有儿女了,咱这可倒好现在连是死是活还都不知道,你倒是去找找啊!”
爷爷说:“你不信有啥用啊,村里人都这么说,连村干部也没办法。”
奶奶不服气:“那你就去公社找找啊,实在不行就到县里,大活人总不能叫尿憋死吧?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弄得咱在村里连头都抬不起来,这不让人活受罪吗?再说了,老二的孩子都这么大了,以后总不能也让孩子背‘黑锅’吧?说他大爷是叛徒”说着说着奶奶又哭了。
为大伯父的事奶奶不知哭了多少次,本来两只挺有神的大眼睛,哭得现在连一点光都没了,看上去明显凹进去了,又小又干瘪,好看的双眼皮也耷拉下来了。
爷爷愁得只是一个劲的低头嘬他的那根老烟袋,过了半天,看到奶奶哭得实在可怜就说:“我不是没找,找来着,过去那些老领导都见不着了,就一帮子小青年在那写大字报,贴大标语。我问他们,你猜他们咋说,你胆子可不小,你儿子是叛徒,那你就是叛徒的家属,没给你定罪就不错了,你还敢来找,快回去吧,再来,也拉你游街去了。你说让我咋办?”
听爷爷这么一说,奶奶不再吱声了,只是不停地抽泣。
奶奶不识字,她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十七岁嫁给爷爷后,是村干部把她在娘家的姓氏前面冠上爷爷的姓,再在后面加个“氏”字,就算是她的名字了。
又沉默了半天,奶奶擦着眼泪叹息道:“唉——,我就不信,早晚得有个结果,老天爷有眼!”
又过了一年,县民政局突然来人送来一张《革命烈士证明书》,并告诉爷爷奶奶,您二老的儿子是为了执行国家的一项特殊任务而牺牲的,他死的光荣,是为国捐躯。从今后您二老就是光荣烈属了,接着把一个《光荣烈属》的红牌牌递给爷爷,爷爷接过牌子强忍着含满眼眶的泪水,低头转身进了里屋。在场的人都明白,爷爷是怕泪水淌出来,让人们笑话。
民政局的人又把抚恤金递给奶奶,奶奶没接,只说了句:“钱俺就不要了,俺儿是为国捐躯的,没给爹娘丢脸,俺就知足了,老天爷有眼啊!”
民政局的人走后,爷爷抱着那块红牌牌,跑到生产队的场院,一个人躲到柴火垛后面,嚎啕大哭起来,是饲养员发现了把他搀回家的。
从那以后,一家人再也不遭别人的冷眼了,奶奶好像比以前也有了些精神,失去了大伯父,奶奶家成了全村第一个烈属家庭。
小时候,奶奶还经常带着我给家里的猪割草,一次,我们回家路过生产队的瓜地时,望着地里那一个个长得滚瓜溜圆的大甜瓜,又渴又饿的我两条腿就像绑了秤砣,再也走不动了。本来我是走在奶奶前面的,可看着看着那满地的瓜就慢慢地落在了奶奶的后面,奶奶回头喊:“快走哇,俺的大孙子!”
我没吱声,一屁股坐在地上撒起娇来:“奶奶,我要吃瓜。”
奶奶摸摸衣兜:“好孩子,奶奶今天没带钱,下次奶奶想着带钱,保准给你买。”
我环顾四周,悄悄对奶奶说:“我去偷一个吧。”
奶奶先是一愣,接着又使劲拍了我一下:“那可不行,偷摸的事咱可不干,丢人!”
我指了指四周,神秘地告诉奶奶:“你看,哪有人呀,保证没事儿,不会有人知道的,你就让我偷一个吧”说完起身就要跑进瓜地。
奶奶使劲把我拉住:“使不得,可使不得,老天爷有眼,你没听说吗,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说完,拉着我绕了一个好大的圈子,来到看瓜的棚下。
看瓜的叔叔见是奶奶,老远就恭敬地打起招呼:“大娘,是您来了,买瓜呀?”
奶奶苦笑道:“哪呀,我今天没带钱,和孙子割草回来,孩子又渴又饿非要吃瓜,我想先跟你赊一个给孩子,明儿个我就把钱给你送来,你看行吗?
看瓜的叔叔听后哈哈大笑:“嗐,瞧您说的,一个瓜值几个钱哪,这么一大片呢,小孩子吃一个算个啥,我给您摘去。”说完叔叔转身就要进瓜地摘瓜。奶奶急忙拦住:“那可不行,这是集体的,俺可不占公家的便宜。”
“大娘,瞧您说的,要是别人那是不行,可您是咱村里唯一的烈属啊,是大功臣。您把儿子都贡献给国家了,别说今儿个孩子吃个瓜了,就是您跟我大爷想吃啥、要啥,只要您老两口跟大队提出来,那都一点不过分,谁也不敢攀比,您说,我说的对不对。”看瓜的叔叔进一步说服奶奶。
“不行,你说的不对,那是两码子事儿,今儿个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让你摘。”奶奶满脸的严肃。
看瓜的叔叔见奶奶那个倔强劲儿,只得说:“好好,我答应您,是买,不白吃。”
第二天,奶奶特意让我给看瓜的叔叔送去五毛钱,可那叔叔说啥也不收,最后我恳求道:“叔叔,你就收下吧,要不回去我奶奶会说我的。”
那叔叔不经意顺嘴说了一句:“那你就别跟她说,问你你就说给了。把钱自己留着买个铅笔本子啥的。”叔叔的话提醒了我,于是就照着他说的去做了。
事后不久,一天,奶奶把我叫到她面前,手里拿着条笤疙瘩问:“你说,那五毛钱哪去了,这么小你就撒谎骗人,长大了那还得了。”
我从没见奶奶这么严厉过。大伯父当兵牺牲了,父亲在东北工作常年不在家,叔叔和姑姑都还没成家,家里就我这么一个隔辈人,又是男孩,所以,平日特别受爷爷奶奶喜欢,不说娇惯吧也是宠爱有加。我万万也没想到奶奶会发这么大的火,吓得直哆嗦,哭咧咧地向奶奶解释:“奶奶,不是我,是看瓜叔叔叫我的,不是我。”
奶奶见我哭的可怜,看样子也确实知道错了,嘱咐说:“记着,以后不准撒谎骗人,不好的事,谁叫也不听,记住了吗?老天爷有眼!”
“记住了。”我看着奶奶,头点得如小鸡叨米一般。
人们都说,小时候的一些事一辈子也忘不了,尤其是挨打的事,事实也的确像人们所说,这次的教训真的让我终身难忘。
上大学,我离开了家也离开了奶奶,以后又参加了工作,走上了领导岗位。尽管工作越来越忙,可是,我始终忘不了奶奶,一有点闲暇,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她老人家,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惦记吧,尤其是爷爷去世后,这种惦记就更强烈了。
若干年后的一个春节,我带着妻、儿回原籍看望奶奶,她可是老多了:笔直的身板缩成了驼背;满头的黒发已稀疏全白,过去犹如碗大的纂,现在已变成像乒乓球一样系在脑后;一口齐整的白牙掉的所剩无几,两腮瘪瘪的,说起话来含混不清,和记忆中的奶奶完全判若两人。奶奶浑身上下把我摸了个遍,又眯着眼脸对脸的看了又看。面对此状,我瞬间仿佛成了一个木头人,呆呆地站在奶奶面前,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有热泪顺着面颊流淌。奶奶问:“你现在干啥呐?”
“在南方一个城市工作。”我贴近奶奶的耳朵告诉她。不知是声音太小没听清,还是奶奶没听懂。妻子赶紧指着我高声告诉奶奶:“他现在当市长了。”
奶奶点了点头,声音颤抖地嘱咐道:“记住,不论当啥长,不论干啥事,坏事不能干,可别给老的丢人,老天爷有眼!”一边说还一边用酷似枯枝的手指,吃力地往头上指。
我大声告诉奶奶:“记住了,您就一百个放心吧!”瞬间又一次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奶奶身边的那些往事。
临别时,妻子拿钱给奶奶,可无论怎么说,她就是坚决不要。
万万没想到,这次相见竟是我和奶奶的最后一面,她离世的那天,我正在国外考察,这也成了我终生的憾事。
跟爷爷奶奶一样,我和妻子也有晚饭后唠嗑的习惯,只不过不同的是,爷爷奶奶是睡前唠,而我和妻子是吃完晚饭接着唠,唠一会再收拾碗筷。
妻子时不时地开玩笑“逗”我:“你看看,人家当了干部,家属亲戚啥的都能沾点光,最起码换个大一点的房子住吧。你再看看咱家,你当了这么多年的干部,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的,身体都累坏了,整个城市都大变样了,可咱家还是老样子,你不觉得亏吗?”
我知道,妻子虽然是在开玩笑,可实际上也是变着法地在发牢骚。看到有的干部一天天在变,再看看自己的丈夫,看看自己的家,心里有些不平衡。每当这时,我也总是开玩笑似的回答妻子:“老婆啊,你说的那些事我要是办起来,太容易了,我一个电话,明天就能让你住上大房子,而且要几套有几套,至于吃的穿的用的嘛,你想要啥我都能给你办到。可是,真要哪一天‘露陷’了,那可怎么办呢?到时候你和孩子哭着喊着去大牢看我啊,你想过那种日子吗?”
妻子使劲推我一把,故作生气的说:“你是真傻呀还是装的,干那种事,哪有让人知道的,不都是偷偷摸摸干的吗。”
我笑笑回答:“是我傻还是你傻呀,‘露陷’的不是大有人在嘛,报纸电视经常报道,你也不是看不到。”
妻子不服气,继续跟我“辩论”:“那都是不会干的,或者说是干得太大了,像你这么有能力,又这么有实权的人,小的溜地干点还能‘露陷’?我就不信。”
我一听特别生气,继续与妻子“辩论”,心想,正好借机开导开导这个老糊涂。我知道,此时给妻子讲大道理她更听不进去,就有意提醒说:“你忘了,我经常给你讲奶奶的故事了,老天爷有眼!”
妻子使劲瞪了我一眼,嘲笑说:“你还领导干部嘞,奶奶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她信迷信,你也跟着信哪,那你给我说说,老天爷是谁?它的眼睛长在哪?是什么样的?看看现在但凡有点权的谁不在‘捞’啊。也就你呗,自作清高,你没听人家说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等你不干了下台了,到时候后悔也晚了。”
我见妻子的情绪有些急,就主动软下来:“瞧你,怎么说说就激动起来了,‘捞’的还是极少数嘛,你这可是一叶障目哦。”
“什么一叶障目,我这叫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你懂不懂?”
“好好,我懂我懂。”女人嘛,都爱在自己丈夫面前站个上风,见妻子这样,我就甘败下阵来,俗话说‘好男不跟女斗’。这次的饭后闲聊就以妻子的“胜利”暂告一段落。
一个月后的一件事,让形势发生了逆转。一天,市里的一位同事突然被上级纪委带走,几天后,为了配合调查,我也被叫去了两天。回来一进家门,就被焦急等待的妻子紧紧地抱住,虽然才仅仅48小时,我已见妻子的面容消瘦了一圈,满脸泪水的问:“你没事吧?”我笑了笑,故意反问:“你说呢?”妻子见我如此坦然若无其事的样子,心里明白了,破涕为笑:“我的妈呀,你走这两天,可把我吓坏了!”我见缝插针,问妻子:“现在我再给你讲奶奶的故事,你应该不会认为是迷信了吧?”妻子点点头:“我不但不认为是迷信,而且还特别佩服奶奶,他老人家真是神啊!”见妻子终于转变了,我内心有说不出的高兴,于是进一步引导:“那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老天爷是谁?它的眼睛是什么样的?长在哪啊?”妻子涨红了脸,尴尬地看着我,然后又故意眨了眨好看的双眸,把嘴贴到我耳边,悄悄地说:“你啥也别说了,我全明白了,都是我的错。”
-
·王国明律师:法律征途上的无畏行者2025-02-06
-
·党员先锋翟进德:责任担当 砥砺前行2024-11-02
-
·退伍不褪色 以善为炬照暖基层健康路——记全国道德教育新闻人物、安阳蓝艺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冯明2026-01-27
-
·红荷映日别样红——访灵宝市作家协会“红色主席”李亚民2026-01-16
-
·法润基层 心向公益——记全国第十二届道德教育新闻人物段宏伟2026-01-13
-
·深耕养生二十载 初心如磐暖人心 ——记公益养生践行者、全国第十二届道德教育新闻人物赵树军2026-01-13
-
·银发逐梦践初心 健康传爱暖基层——记“宝姥姥”田书霞:以向善之行铸就基层道德标杆2026-01-12
-
·风口上的职教追梦人 安阳学子的高薪引路人——记全国第十二届道德新闻人物周兰英2026-01-12
-
·暴雪背后的“提案密码” 政协委员的暖心守护2025-12-15
-
·“韦一趟”是怎样炼成的2025-08-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