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当代实力派优秀作家 王志娇
更新时间:2024-09-19 关注:3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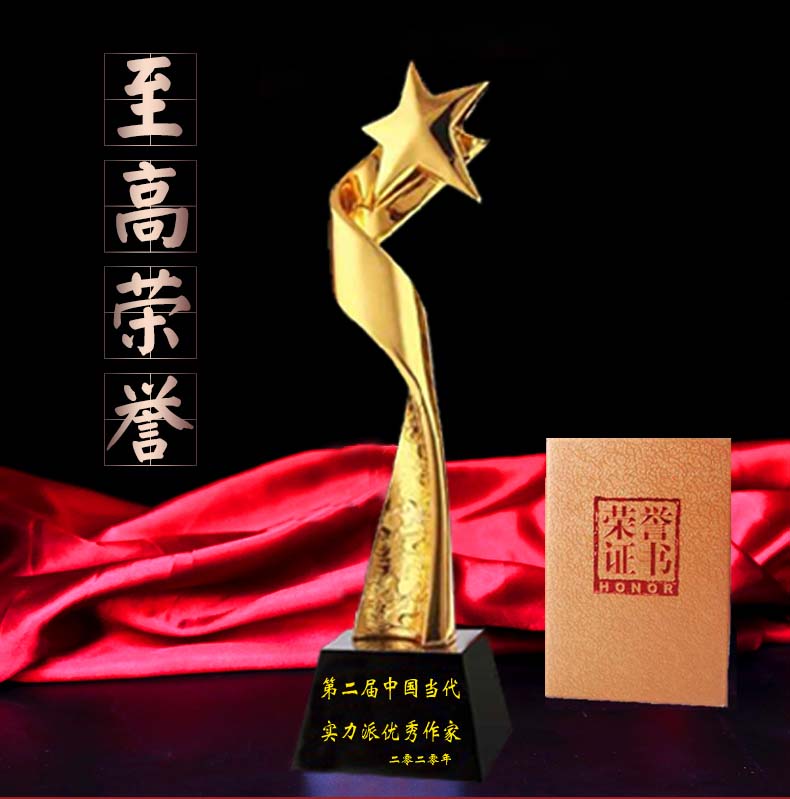

王志娇,笔名男孩儿,90后女孩,语言学在读硕士,作品《我与父亲谈了场恋爱》《生命告白》《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致再见·前任》《爱像风筝断了线》和论文等散见于国家级报刊杂志及文学网站。
作品赏析
世界予我的第八个清晨
文/王志娇
我喜欢牵着父亲的手在路上行走,太阳爱我,他也爱我。
我也渴望成为一片大陆,在他的注视下,手捧着,一簇鸟语,两盏花香,大摇大摆地,穿梭于茫茫花的海洋。
我喜欢骑在父亲的脖子上,在云间穿梭,一边牵着虞梦,一边曳着雨滴,一面畅游未来,一面滋润父亲种下的希望。
我也渴望化作一朵胸前的黎明,披着粉红色的外衣,在父亲的宠爱下,接受黑夜,迎接辉煌。
我时常赤足于时间的河流之中,享受时光从脚趾缝间川流不息的即视质感,偶尔向着河岸那畔的父亲遥遥相望,这再熟悉不过的旧世纪丰碑,正是世界赠之予我的第八个清晨。
小时候,读不懂顾城的诗,更读不懂父亲为什么总是起早。
以往的岁月静好,常常是还未拂晓,即被父亲叫醒,然后心甘情愿地从暖暖的被窝中爬起,默默地感受着父亲起早的完整经过。哦,原来父亲就是这样每日追赶月亮的!
自古以来,北方的冬夜浑身是雪,那雪堆砌得整整齐齐,都延续在父亲棕褐色的铁锹上,一锨一锹,上升下落,就着古老而传统的扫帚有节奏地在半空中挥舞,继而伴着一条条清晰而宁静的雪道,自南至北,由东延西,似乎正在等侯远方重要的来客,又像是于平日里在大地之上弹琴种花的消遣,那吱呦吱呦的“琴声”犹如仙境里的天籁,“应是天仙狂醉,乱揉碎了白云”,日出皓兮的鸡鸣,是心之所善,亦是余襟浪浪。日里的雪仿佛是陪伴在孤独父亲身旁的白月光,她那么近,那么静,和寡言的父亲一样,果不其然,真正的爱又怎能轻易掂出它的沉甸?
转而,我牵制住内心飞絮的思路,这才听到了父亲按下水闸的声音,踩着厨房里不绝如缕的切菜声,哗啦哗啦,可喜,可愕,可歌,可泣。
这熟悉的一幕,串着酸甜苦辣的光阴与生命拔节的繁华,竟在我不大不小的记忆长廊间残存了十几年之久,如今不经意间摸起那本泛黄的日记,却恍若一下子回到了童年的光景。小时候的脑海内缺失了叽叽喳喳的玩闹,却偏偏丝毫不觉晦涩,犹如我和父亲之间的爱,终归是经得起岁月的弹劾,沉默间发出阵阵迷人的声响。
春末夏初起早挑瓜,是我对清晨与父亲的又一抹记忆。
我自幼“遗传”母亲,最爱吃瓜。于是,每逢暮春之际,父亲便早早地驾着那辆村里最耀眼的摩托车,带我去升阳的瓜地里买瓜。
我不知道父亲为何偏偏挑中早晨的时间前去那么远的地方买瓜?或许是因为他怕耽误上工?还是清晨的瓜最为香甜?亦或是单纯地为了让我跟着起早?
父亲是个粗心的父亲,但对要带回家的“宝贝”可谓是精挑细选,目光所及时而像丘比特的爱神选箭,时而像挑选荔枝的醉酒杨贵妃。父亲对钱之类的俗物向来粗手粗脚,自是对瓜的价格不拘小节。他时常一边选一边叨唠:“选瓜如选人,重在看心、看品质,看他内心的缺失,正是从这瓜秧下的根得来。”
母亲听了,便不解风情地调侃到:“这样说,以后你得亲自为女儿挑中个好女婿呢。”
父亲停住了掰瓜的手,一屁股坐在自家庭院葡萄架下不到半米高的板凳上,“女儿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她的世界大着嘞。她的事情她自己做主,当父母的,相信她,索性就让她放开手脚去闯。”
我虽表面上若无其事,心里却对父亲一副高风亮节、成竹在胸的模样嗤之以鼻。“做父亲的,当真不怕女儿被骗?不怕我抓个大逆不道的“地痞野兽”回来,丢人现眼不成?”
买瓜回来的路上,太阳的腰已经抻起老高,我坐在父亲摩托车的后盖上,一时间很是恼苦,为什么视线之内仅夹着整箱零一袋的瓜,而我却冥冥觉得,自己与父亲的距离好远好远。我总是害怕“不爱我”的父亲,要瓜不要我;后来长大一点,依旧担惊受怕,生怕粗枝大叶的父亲丢了我,也丢了瓜。
因为起早买瓜一事,我没少向母亲告状。今天状告父亲半路把瓜摔了,明天或许就是为了赶工忙,开了快车的说辞,总之有母亲撑腰,我便可以理直气壮地“为所欲为”。纵然我说什么,父亲依旧沉默不语,可越是这样,越引得母亲发笑,前仰后翻间当众指责父亲,不会照顾孩子,说是再也不要我跟着父亲起早了。我听了,当时便直觉得晴天霹雳,“为什么小聪明一世,却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家的脚?”
其实,父亲虽然表面上不言语半字,却总是偷偷地向母亲禀告我的进步,“不用担心了,勤奋着呢,看瓜的眼光精准不少呢,还会讨价还价,总帮我跟人家老李讲价,省下不少钱都被她给私吞了。”
“眼神也好,瓜农老李一股劲儿地总‘夸’她,说是让我买瓜自己来,千万别带‘老佛爷’。”
“小佛爷咋又来了,你别来了,买瓜不讲行情。到我地里来,大瓜,好瓜净你挑,还得折扣好几毛钱,以后得嫁到我们家来当童养媳,不然你爸的瓜,我老李贵贱不卖!”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搬出“祖传”的看家本领彻底和他杠上。关于彼时耍乖卖宝的斑斓记忆如今早已模糊不清,只见得那时的日记仿佛格外丰盈而晴朗: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想擦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清晨。”
老李一边哈哈大笑,一边给父亲点烟,嘴上不停地夸我既机灵又勤奋,小小年纪就能起大早,跟着爸爸跑出大老远的地方选瓜。“自古得天下美瓜而尽妻之,瓜都这样大,到底是要带走哪一个才好呢?”
多少次临走之时,老李盯着衣兜里被我顺走的瓜,生要把我从父亲的摩托车上拽下来,我吓得大哭,大吵大闹之际,这才和卖瓜老李结下了死敌。
以后的以后,每一次选瓜,我都早早地爬上父亲的摩托车。任谁生拉硬拽,死也不放手,导致现在每逢夏季捧瓜的时候,我都情不自禁地对仇人老李思念有加,想知道他现在身体怎么样,还凶不凶,抠门不抠门。
现在的我,也正努力地学着跟父亲一样起早,学着和他一样,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一样地追着夜晚的月亮四处逃跑,但却唯独没了父亲拉着长长的大门的声音和开闸放水的自然回响。印象中,父亲独自吃着自己做的早餐,咂米粥的声音骚动着我们快快起床,现下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让越来越多的人晚睡晚起,她们错失了一日之计里多少个美好的开始,又在多少个夜里孤影自怜地收拾着现实摔在地上的邋遢而过去的碎影,然后日夜兼程,重蹈覆辙。我亦飘零久,清醒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走了那么远 /我们去寻找一盏灯 /你说 /它就在大海旁边 /像金桔那么美丽 /所有喜欢它的孩子/都将在早晨长大
自古黎明与清晨之间时有交叉,从凌晨到拂晓,从拂晓迈向黎明,第一次觉得时光可以这样清晰,这样慢而满,这样美,这样奥妙,这样举世无双。粗茶淡饭的日日打磨下,父亲的清晨就着柴,柴就着油盐酱醋,一齐穿越布满皱纹的烟囱,化作永恒记忆里人间烟火的古老尘味,令人再熟悉不过。多么希望起早的人能多一点点,以此,人生的遗憾也就减少一半。
未来的路上,我还要结识好多好多的人,和好多好多的事。父亲的早起不是热情,更无关勤奋,不过是年深月久,早已凝做爱的礼物,成为了我和母亲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弥足珍贵地镌刻在手掌的生命线,怀念,抑或寻找,来日方长,时间,会让强烈的东西愈加深刻。
未来的日子里,我还要遇见好多好多个清晨,过去是我的,那属于我的未来,也定只有独一个。我会未来着每一天的未来,读城市衰落,盼日出复活,看春江晚景,送秋景萧疏,我愿换装成海上的大鱼,和勇敢的海棠一起,怀着感恩的新奇探知人类世界的另一个海底。我多么希望,有一个永远到不了清晨的清晨,一晌梦,一阵风,我只用指尖,触了触阳光,醒来时和父亲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流浪”孩子与牧羊犬
文/王志娇
“谁家庭院自成春,窗有莓苔案有尘。偏是关心邻舍犬,隔墙犹吠折花人。”这是父亲读给他的最后一篇打油诗。突如其来的车祸,使男孩失去了唯一的至亲,他17岁,一贫如洗的小家却还是依然富有,富有到唯独拥有一只牧羊犬。
这儿远离闹市区的喧嚣,黛色的瓦墙,泥砌的栅栏,还有大片大片的芳草地,恍若城堡中的庄园,梦幻而古典,那是一种罗切斯特式不掺杂质的美,男孩微倚着体格健硕的德国黑贝,眼神之中似有偏离惆怅与等待的失落。牧羊犬一月之多,笑不露齿,似乎胸有成竹,训练有素,黝黑发亮的脸庞、厚毛、竖耳、杏眼,搭配结实有力的肌肉,锋利的四爪似是有意隐藏着内心的沉重与凶猛。若近瞧,其肩脊笔直,背披黑灰,腹埋咖啡豆一般的棕黄;若远望,则各部位和谐而匀称,端庄而高雅,胜于刚柔并济,却丝毫不似盛气凌人。此时,它正依偎在主人面前,风情万种地咀嚼着咬胶,那磨牙声柔柔细细,流淌在唇齿间似点露着绛珠仙草的万般愁情,周围散落着的,是几枚干燥的狗粮和十多张带着父亲笔渍的生日贺卡,另一旁,松脆的干肉饼悄悄地学着牧羊犬的模样,颐指气使地赖在草地上晒太阳,暖风定然吹不走,这聪慧,这忠诚,这一脸憨态,这甘愿臣服......
“黑贝,你会唱生日歌吗?记得每年,父亲和你都会一起给我过生日,我很想他......”哽噎的话音遮挡了前来报道的乌云,沉沉的天空似乎一秒间恢复了往昔的光亮。
“现在家徒四壁,我穷寒得只剩下你了,但......是不是也算一种幸福呢!”说着,黑贝悠哉游哉地窜进了男孩的胸膛,托着一脸的笃定与沉醉,迎上献吻。
“在家要照顾好自己,要吃饱,要睡足,好吗?......”我会让杨奶奶来看你,人类中,你只可以相信她。”男孩转身上车,留下了一路追着跑的黑贝和狼藉满地的思念。
这是他们第一次分开,高二的男孩总要独自背着书包去偏远的郊外求学。除去规定节假日,一个学期只能回家一次。
彼时,白日西沉,曲曲折折的回忆深处,是流年雕刻的印影与父亲讲过的数不胜数的狼犬故事,对比而今现实冷清,也唯有黑贝能够在贫瘠的岁月里散发出永恒的光鲜与魅力,抑或是在遥不可及的黑暗中熠熠生辉。可每每想起英年早逝的父亲,那暗无天日的团团阴霾,那并肩作响的灼烧与疼痛,使他再也不敢过马路,不敢看车来车往,不敢想川流不息,不敢深信不疑,更不敢全然依赖。后来,慢慢地,竟是黑贝陪他成长,左右庇护,直至他战胜恐惧,重启希望。自此,即使是为了黑贝,那双童真的眼睛也断然不会轻易落泪。
曾几何时,他学着父亲写蘸挂深情的文字,那由琐碎拼凑而成的厚日记恰如旧约圣经里的诺亚方舟,载满了岁月悠悠和“流浪”男孩与牧羊犬的点点滴滴:
“今日午后,我们外出散步,谁知,于冷血的旁人而言,黑贝居然成了‘穷凶极恶’的敌人,无辜地被定下了‘恐吓’婴儿的罪名,莫须有的威胁一度令我陷入了两难境地,这时,又是黑贝拯救了我,它主动地趴在地上认错。我也只好配合着‘狠狠’打它。由轻到重,再由重到轻,灵巧的“笏板”在来自宽恕之情的半空中来回挥舞,羞愧的泪水促成了模糊视线的横流,岂不知,它凌厉冰霜背后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出于对弱小的我的保护,这一点,我又怎能不知不懂?”
“我时常渴望成为低空中游散的云彩,没有悲欢,亦不必焦躁,然后任性地,随你远行,带你驰骋。”
“又或者我是你,代替你受伤,像你陪伴我一样,从来不曾孤单过。”
诚然,从冷酷凶残的亚洲狼被驯化至今,割舍之途可谓漫长而艰苦,历史荒芜的硝烟重重,狗无疑脱离了祖先的群居天性而成为了宇宙孤独至极的存在——没有亲人,没有伴侣,没有后辈与自由,更没有除主人以外的任何朋友,在人类眼球中那缠绕得千丝万缕的七情六欲,在犬类尤为短暂的生命线中竟空白得如此可怜,有声的世界里,吠声自然而然地成了它们唯一的语言......
每一次杨奶奶打来电话,男孩都能听到熟悉的声音,那牵动人心的想念,沿着长长的老式电话线放浪翻滚,而后便在稀薄与艰巨的两极间勾留辗转,同频共振。
冬去春来的光阴,若白驹过隙,倏然而已。男孩迈入高三,模糊不清的未来遥远而笨重,内心对黑贝的惦念与愧疚自是愈发响烈。多少次烟雨茫茫,东风怀愁,他都想起那个永远走在自己前面的黑贝,那个支持他、并永不悲伤地走向远方的牧羊犬。 百感交集之际,他又欲说还休,只得死死地攥紧了手中的笔,口不绝吟地,投入到了新一轮的战斗当中。
冥冥中,却不知为何,男孩似乎预感到一股呼吸声正由远及近,带着些许急张拘诸的气势,朝自己这边的磁场席卷奔来。
“是黑贝?”
“不!不会,这么远,黑贝也早已不再年轻......”男孩立马否定。
“只是......这声音愈近愈像,竟还自动踢踏着生日歌的节奏”。男孩猛然掰开隐匿在校服袖子里的手表——“不偏不倚”,今天正是见证他驻足人间18年的生日!
“黑贝记得!它......是特地赶来给我过生日的!”
牵扯着慌张的思绪,男孩箭一般地冲出教室,见到黑贝的那一刻,男孩激动得涕泪滂沱。在青草还未葱郁的操场上,他隆重地举行了自己的成人仪式。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黑贝,想它曾也一身英俊、两方“枭雄”,如今老之将至,睿智的眼神却愈显清透。只见它慢悠悠地扭过去,憨态可掬的笑容中浸满了得意的欢喜。春风拎笑,吹过它黑黢黢的鼻毛,那掠过骄傲的唇和略带苍老的剪刀状咬齿于无形之中毅然拧成一种默契的过渡。曾经通体和谐、体毛直硬,如今密布在外,延展不一;曾经后腿富毛、前腿径直,如今铁汉垂暮,分外有力却也几度沧桑,潇洒多姿却也敏捷有度。微微上翘的尾巴流溢着凹凸起伏的弯曲,在百花争艳的春日仍旧可圈可点。包裹的人群缝隙里,只窥见一条毫无褶皱的舒展弧线从耳尖途经背部抵达至此,悠悠晃晃,时隐时现。它将含着的生日五彩灯立放在男孩的脚边,伸长脖子,轻轻地搭落在主人的双肩,后将其深拥入怀,那原本紧密的脚趾间,似呈半圆状的拱型,却碾磨着长途跋涉的磨损。想必,此间所有不紧不慢的温存,定会从日后许许多多的夜幕中寻得一个看似平凡的角落,然后默默陪伴,坚坚挺挺,然后长相厮守,战胜、倔强。
假以时日,犬日将尽,鼻息无存,它便幻化成一颗牧羊星,镌刻在主人的心头。所以,男孩也并不空空如也,而是牵着与牧羊犬的回忆,在黑夜尽头踽踽独行。纵然一路流浪也常有伤痕,但内心积攒感动的小河,怕是一辈子都刻骨铭心。所谓生命,大概是一次又一次送别,黑贝纵然是他的青春,他又何尝不是黑贝的整个世界?
试问黑贝:为何你的眼里常含泪水,是对这“世界”爱得深沉?
-
·王国明律师:法律征途上的无畏行者2025-02-06
-
·党员先锋翟进德:责任担当 砥砺前行2024-11-02
-
·退伍不褪色 以善为炬照暖基层健康路——记全国道德教育新闻人物、安阳蓝艺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冯明2026-01-27
-
·红荷映日别样红——访灵宝市作家协会“红色主席”李亚民2026-01-16
-
·法润基层 心向公益——记全国第十二届道德教育新闻人物段宏伟2026-01-13
-
·深耕养生二十载 初心如磐暖人心 ——记公益养生践行者、全国第十二届道德教育新闻人物赵树军2026-01-13
-
·银发逐梦践初心 健康传爱暖基层——记“宝姥姥”田书霞:以向善之行铸就基层道德标杆2026-01-12
-
·风口上的职教追梦人 安阳学子的高薪引路人——记全国第十二届道德新闻人物周兰英2026-01-12
-
·暴雪背后的“提案密码” 政协委员的暖心守护2025-12-15
-
·“韦一趟”是怎样炼成的2025-08-03






